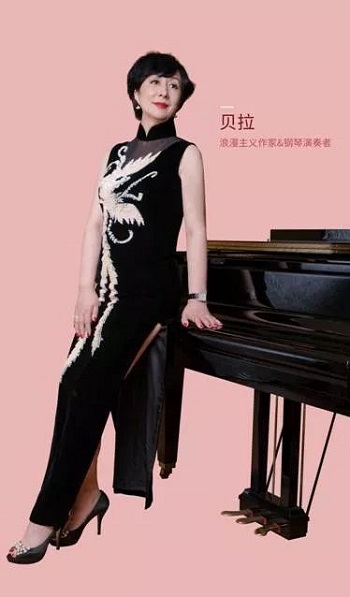
记者:你的“大阪世博会演讲稿”在华人头条与日本关西华文时报的浏览量已超200万,影响力很大。通过阅读你的文章感受到日中友好的必要性。
贝拉: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日友好源远流长。樱花与牡丹共枕同一片月光,汉字在丝绸上跋涉千年已成为两国文人砚台里的墨痕。当大海的浪涛将两国命运织成经纬交织的锦缎,多么希望让遣唐使船队满载的星光去辉映千年的中日文明长卷!
记者:你的演讲活动现在安排在何时?
贝拉:演讲活动原先安排在世博会开幕日当天。现在争取五月底。主要是在等一件非常重要的中日友好信物——由日本顶级金壶大师大渊武则先生制作的一公斤纯金壶从上海运往大阪。这是我孩子的藏品,用于捐赠给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日中友爱”文化交流项目。
记者:您谈到伟大与苦难共存,你从小被引导从裂缝里看见光的信仰影响了你的人生观。
贝拉:我是属于那种在胸腔里豢养着星辰的人,生命深处永驻着晨曦,如但丁穿越炼狱时窥见的圣光;纵使我在暗夜中坠入海洋,圣艾尔摩之火仍在我灵魂的穹顶跳着不朽的芭蕾,我随她的红舞鞋滑向彼岸。
记者:《魔都云雀》是否是你真实生活的写照?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贝拉:这是迄今为止最接近于我真实生活的书。这场载入人类悲情史的疫情改变了世界,虽然这座城市早已恢复了它的繁华,但不一样了。很多东西在时代变迁中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重生与蜕变。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3年6月18日,东京银座小巷里那间我们常去的旧唱片咖啡馆。那个沿街的落地窗凝着梅雨季的氤氲,他手指无意识地划过玛奇朵斑驳的玻璃杯沿,轻轻抚起金丝眼镜微微滑落鼻梁的模样,与18年前在上海我们相遇时完全一样。他衬衣袖钉与柚木桌面摩擦的金属声,像是某种即将消逝的摩尔斯电码……
记者: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贝拉:他曾诙谐地说自己是沿着电话线爬出上海贫民窟的鼹鼠。家中客厅的飘窗上永远放着那本《下里巴人的挽歌》——万斯初版精装本的烫金标题在他眼里是一把推开童年之门的钥匙。每一次他读到第三章时都会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没想到如此正直厚道的国际电信专家会被时代的风暴卷走;他是一位捐出自己千万年薪资助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与捐助养老院、弱势群体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悲情与苦难成就了这部作品。《百年孤独》对这本书的创作影响最大。
记者:你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预期?上海特殊时期下的爱情悲剧让我想起《霍乱时期的爱情》;题材上就已吸眼球了。你如何以浪漫主义去表现现实题材?
贝拉:上海特殊时期的爱情题材确实吸全球眼球。但判断作家的尺度不在题材的选择,而在灵魂的深度与艺术的完成度。我是一个跳动着自由灵魂的作家,也是苦难见证者。但凡伟大作品,都是作家将精神骨折处重新接续时所生长出的思想骨痂。伟大的写作永远在叩击存在本质,就像马尔克斯让马孔多的雨季既淋湿独裁者的权杖,也浸润人类永恒的孤独。作家的使命不在于选择立场,而在于用文字的棱镜折射时代光谱。而巴黎街头的咖啡馆里,萨特曾用烟斗敲打着《存在与虚无》的扉页说:”文学就是介入。”这位存在主义大师的断言如手术刀般剖开了作家的责任内核。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随着阅历增长,我对鲁迅越来越敬仰,他那种中华民族硬骨头的精神是这个时代所终极匮乏的脊梁。
这部近三十万的书我做到了无愧于自己的灵魂。我没有多余笔墨写那场疫情本身,就如卡夫卡从未描写集中营,却预言了整个世纪的生存困境。
我与翻译家们都非常有信心,我个人尤其看好日本市场。因为不少故事情节与心路历程与日本有关。我是在日本疫情爆发封国前乘坐最后一班日航离开东京的;我也是日本国门开放后全日空首航乘客抵达东京的。这部以一座城市一对夫妻的命运转折来反思这场疫情下人类如何获得重生。我在写到三无产品的午餐肉物资,那铝罐表面的水珠像川端康成雪国隧道尽头闪烁的银河时哭了很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受文字以外的叹息。人道主义是生命的内核。
记者:能否概括你这本书的主题?
贝拉:所有苦难都通向日出,漂泊者的玫瑰,在世界的伤口种植故乡。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